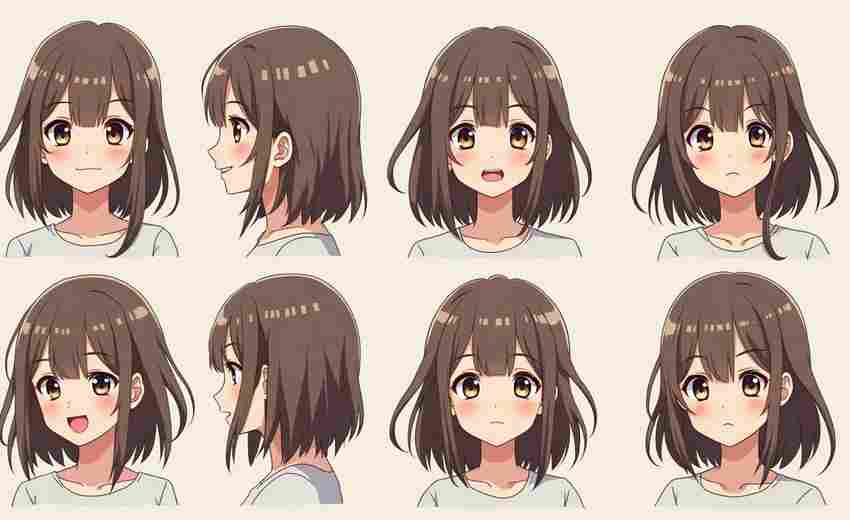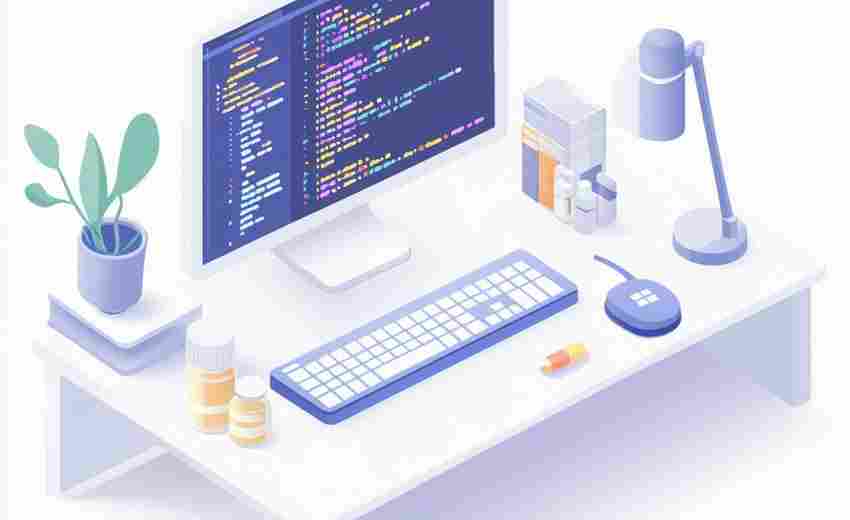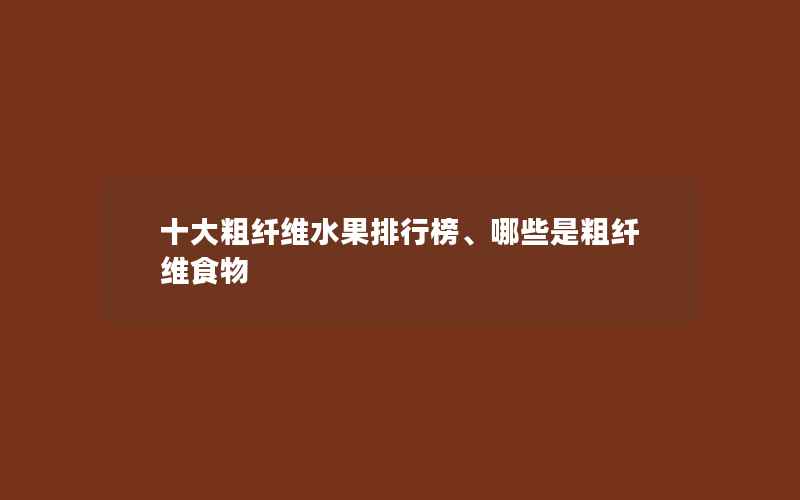哪些合同条款属于过度免除经营者责任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合同条款的公平性是保障交易安全的核心要素。部分经营者利用信息不对等优势,通过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将自身责任不合理转嫁给消费者。此类条款不仅违背契约精神,更直接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亟需通过法律规范与司法实践予以纠偏。
一、单方免责声明
经营者常通过单方声明规避基础义务,例如“商品售出概不退换”“快递损毁不担责”等表述。这类条款看似明确,实则通过格式条款预先免除经营者的法定责任。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经营者不得通过格式条款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否则相关条款无效。例如在网络购物中,某平台以“签收即视为商品完好”为由拒绝退货,但消费者拆封查验属于行使检验权的正当行为,经营者以此限制消费者权利的行为已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无效条款。
司法实践中,此类条款的效力认定存在三个判断维度:一是经营者是否履行显著提示义务;二是免责范围是否超出合理限度;三是消费者权益受损程度。北京三中院审理的快递保价条款纠纷案中,法院认定保价金额显著低于实际货值的条款因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而无效,突破了传统“保价即限责”的行业惯例。
二、限制消费者权利
部分合同条款通过技术性设计压缩消费者选择空间。例如会员协议中“自动续费不可取消”、购房合同中“开发商享有单方解约权”等约定,均属于通过不平等条款限制消费者救济途径。这类条款往往嵌套在冗长的合同文本中,消费者在签署时难以察觉其不公平性。江苏姑苏区法院审理的知网最低充值案中,9.8元的最低充值限制被判定侵犯消费者财产自主处分权,成为数字经济时代限制性条款司法认定的标志性案例。
法律规制的难点在于区分合理商业安排与权利侵害边界。日本《消费者契约法》将“赋予经营者单方合同解除权”明确列为不公平条款类型,我国司法实践亦借鉴该标准,在商品房买卖纠纷中否定开发商任意解约条款效力。但需注意,基于风险防控设置的合理限制条款(如特殊商品七天无理由退货例外)不在此列。
三、模糊条款规避责任
利用语义歧义设置责任陷阱是新型免责手段的典型特征。某在线教育平台协议中“课程内容调整不另行通知”的条款,以及旅游合同中“不可抗力包含临时管控”的扩大解释,均属于通过模糊表述扩大免责范围。这类条款的隐蔽性更强,消费者往往在权益受损后才意识到条款解释权被经营者垄断。
司法解释通过双重标准破解此类难题:一是采用“通常理解”解释原则,排除经营者单方释义;二是适用“不利解释规则”,当条款存在两种以上解释时,采纳不利于条款提供方的理解。上海某健身房“会籍有效期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的条款,即因违反解释规则被法院认定无效,经营者需全额退还剩余会费。
四、技术手段强制交易
数字经济发展催生出新型强制交易形态。部分网络平台通过默认勾选、弹窗诱导、界面跳转等技术设计,迫使消费者接受捆绑服务或附加条款。某视频平台“关闭自动续费需连续点击七层菜单”的设计,本质上属于借助技术手段实施的变相强制交易。这类行为已突破传统格式条款范畴,构成对消费者选择权的实质性剥夺。
监管层面正通过专项治理强化规制。市场监管总局2024年开展“网络交易格式条款清朗行动”,重点整治隐藏同意选项、虚假倒计时提示等十二类技术性强制交易行为。司法领域则通过扩展解释《民法典》第497条中“技术手段”的内涵,将界面设计纳入格式条款效力审查范围。
上一篇:哪些功能障碍表现提示脚后跟骨裂较为严重 下一篇:哪些品牌笔记本在抗压性能上表现较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