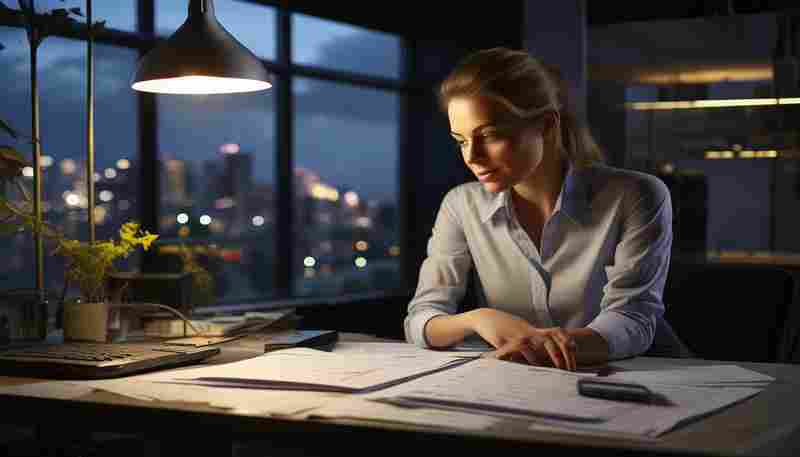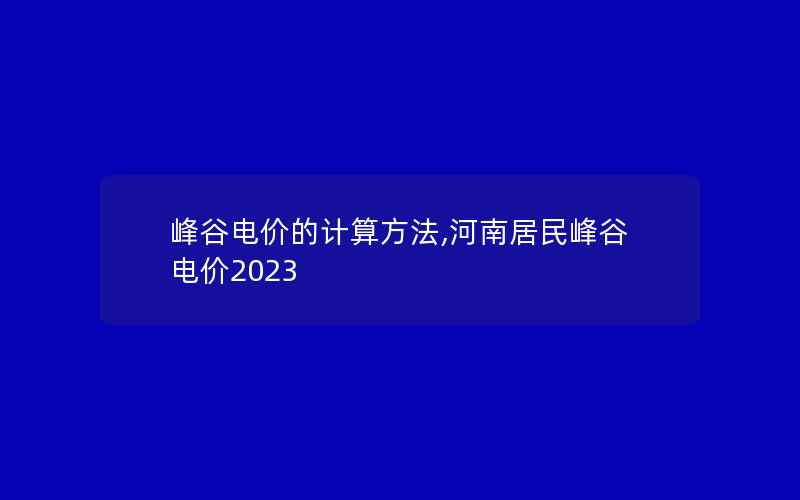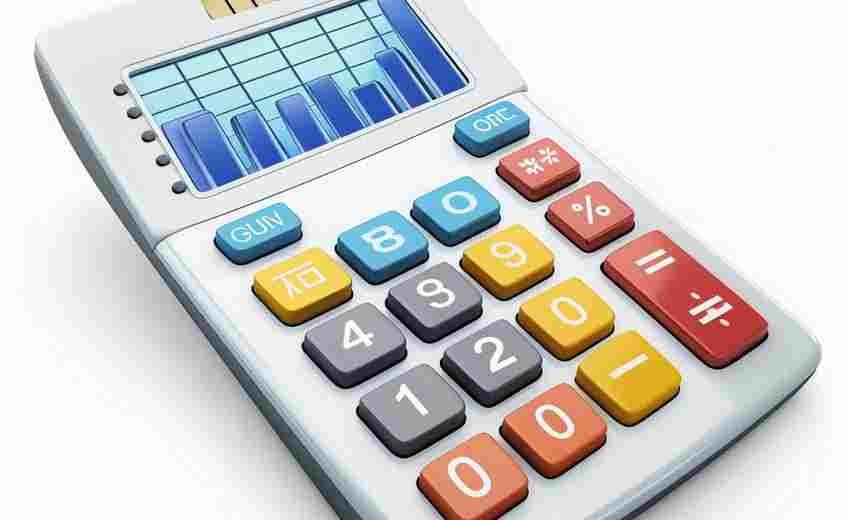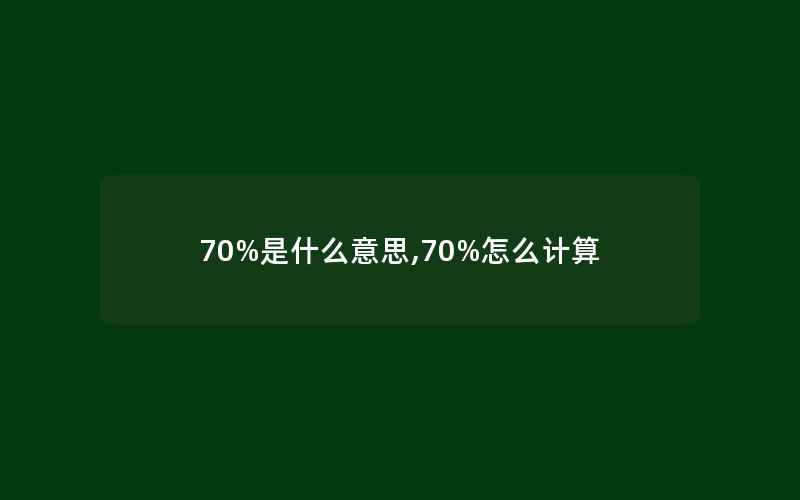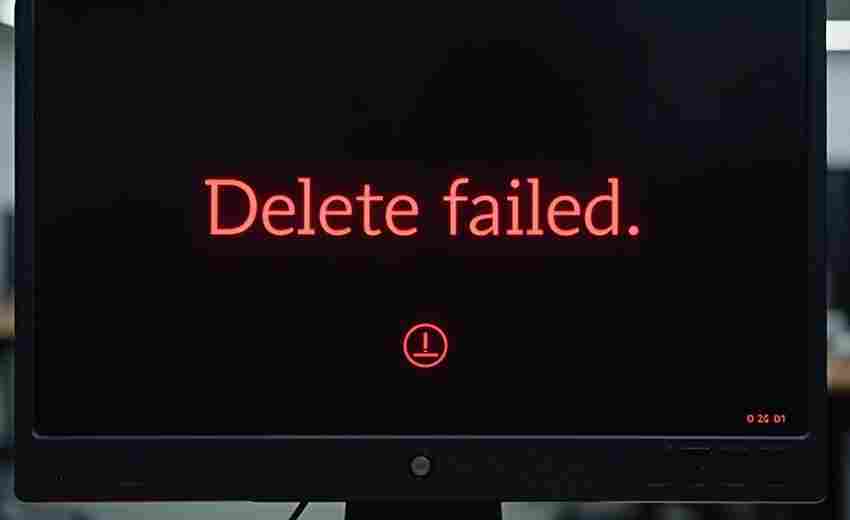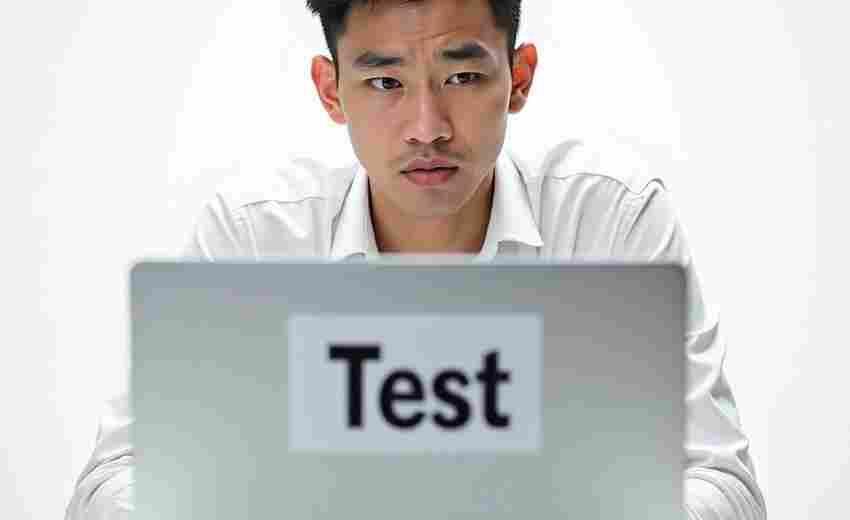加班费的计算基数如何确定
在劳动关系中,加班费的计算基数直接影响劳动者的实际收益与用人单位的用工成本。由于法律未在全国层面统一标准,司法实践中需结合合同约定、工资结构、地方规范及裁判尺度综合判断。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既源于立法模糊性,也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劳资博弈等因素密切相关。
合同约定的效力边界
我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一条虽规定加班费支付义务,但未明确计算基数。《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三条允许用人单位与劳动者通过劳动合同约定加班费计算基数,但需满足两个核心条件:一是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二是应覆盖劳动者正常劳动时间的固定收入。例如,在(2015)民申字第610号案例中,最高法院认定大连某公司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基数合法,因其符合辽宁省地方规范且不低于法定标准。
合同约定并非绝对有效。当劳动合同仅约定基本工资而实际发放的工资包含岗位津贴、绩效奖金时,法院可能突破合同约定。如(2015)浙杭民终字第1140号案件中,法院认定企业以基本工资为基数违法,因工资条显示存在固定发放的全勤奖等补贴,需以实际收入为计算基准。这种司法裁量体现了对劳动者权益的倾斜保护。
法定标准的底线约束
无论合同如何约定,最低工资始终是计算基数的刚性底线。北京市高院在(2017)京高法发142号文件中明确,双方约定低于最低工资的条款无效,应按法定标准执行。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5条进一步规定,折算后的小时工资低于最低标准的,需以最低工资为基数补足差额。
结构性工资的拆分策略常引发争议。部分企业将工资拆分为基础工资与各类补贴,仅在合同中约定基础工资作为基数。但根据《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十四条,若拆分后的基础工资低于实际工资70%,法院可能认定该约定显失公平,需以实际工资总额重新计算。这种裁判逻辑旨在防止企业通过工资结构设计规避法定义务。
工资构成的认定规则
奖金、津贴是否纳入计算基数存在地域差异。上海高院在《企业工资支付办法》中要求,凡属固定发放的岗位津贴、交通补贴均应计入基数,而绩效奖金则需根据实际发放周期分摊计算。反观广东地区,粤高法(2016)1号文件允许企业通过集体合同约定将部分津贴排除在基数之外,但需经工会协商程序。
对于提成制员工,司法实践采用动态计算法。江苏省高院在(2017)苏民申2911号裁定中确立规则:提成工资应按实际发生月的平均值计入加班费基数,而非简单取年度平均值。这种方法既保障劳动者权益,又避免企业因偶然性高收入月份承担过高成本。
地域规范的差异化实践
北京、深圳等地认可约定优先原则。根据京高法发〔2024〕534号文件,只要约定基数不低于最低工资且未明显偏离正常工资水平,法院一般予以尊重。但上海实行更严格的“实际履行主义”,《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第九条要求以劳动者实际获得的全额工资为基准,合同约定仅作参考。
中西部地区呈现混合型裁判倾向。重庆市五中院在(2022)渝05民终1762号判决中提出“双轨制”标准:合同约定基数高于实际工资70%时从约定,低于该比例则按实际工资计算。这种折中方案试图平衡劳资双方利益,但客观上增加了司法裁判的复杂性。
司法裁量的价值平衡
最高法院民一庭在《劳动争议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强调,加班费具有经济补偿与健康权保护双重属性。当约定基数显著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时,即便符合最低工资标准,法院仍可能启动实质审查。例如(2023)沪01民终4587号案件,法院以餐饮行业平均工资为参照,认定企业约定的基数虽合法但不合理,判决补发差额。
举证责任分配影响基数认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劳动者对加班事实承担初步举证责任,而用人单位需对工资构成、计算方式等提供详细证据。若企业无法提供工资拆分依据,法院通常采信劳动者主张的实际收入数据。这种证据规则倒逼企业完善薪酬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