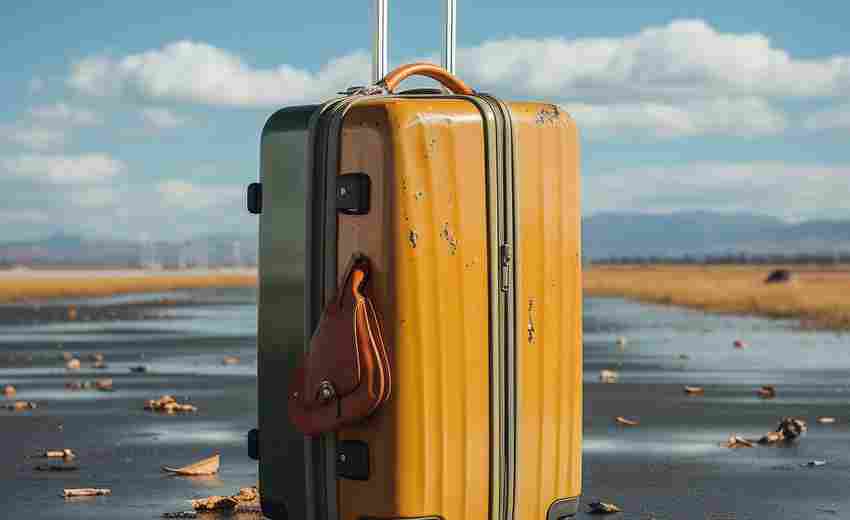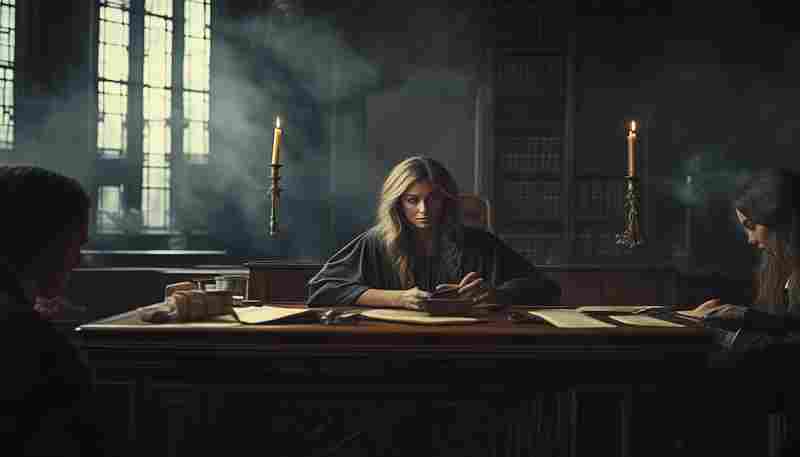抵押权人能否干预抵押房产的租赁行为
在不动产交易与金融担保领域,抵押房产的租赁行为与抵押权实现之间的冲突始终是实务难题。随着《民法典》对“抵押不破租赁”规则的调整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完善,抵押权人对抵押房产租赁行为的干预边界逐渐清晰,但实践中仍存在权利平衡与法律适用的复杂性。
一、设立时间的法律效力
抵押权的设立时间直接决定了其对租赁权的对抗效力。根据《民法典》第405条,抵押权设立前已存在租赁关系且承租人完成占有转移的,抵押权人不得对抗租赁权。这一规则延续了物权法第190条的核心精神,但通过增加“转移占有”的要件强化了权利公示要求。例如,某银行在办理房产抵押登记时,若承租人已实际入住并缴纳水电费,即便抵押合同签订在前,只要抵押权登记在后,租赁权仍可对抗抵押权。
相反,若抵押权登记早于租赁合同成立时间,则租赁关系不得对抗已登记的抵押权。抵押权人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28条,申请法院涤除影响抵押权实现的租赁关系。2023年重庆某法院审理的案例中,抵押人将已抵押的厂房出租给第三方,法院审查发现租赁合同签订于抵押权登记之后,最终裁定涤除租赁关系进行拍卖。这种时间优先原则的确立,有效遏制了抵押人通过倒签租赁合同规避债务的行为。
二、租赁对抵押物价值的影响
租赁权是否实质减损抵押物价值,是判断抵押权人能否干预的核心标准。根据司法解释,若长期租赁导致抵押物拍卖价格显著降低或引发流拍,即构成对抵押权的“不利影响”。例如某市不动产拍卖案例中,抵押房产附带十年租约,导致评估价较市场价折损40%,法院据此支持了抵押权人涤除租赁的申请。这种价值判断需结合租金水平、剩余租期、承租人经营状况等综合评估,而非单纯以租赁关系存在作为干预依据。
对于价值影响程度的认定,实务中存在主观与客观标准的融合。一方面,需听取抵押权人关于租赁减损价值的举证,如专业评估报告、同类标的成交数据对比;参考《民法典》第726条确立的“同等条件”规则,若带租拍卖可能排除潜在竞买人,即便抵押权人未直接主张,法院亦可依职权审查。这种双重标准的运用,既保障了抵押权人的优先受偿权,也避免了过度干预市场交易自由。
三、司法实践中的裁量边界
法院在涤除租赁关系的程序中,需严格区分程序审查与实体认定。根据(2009)执他字第7号答复,执行阶段不得直接否定租赁合同效力,仅能通过“解除占有”实现权利剥离。某地方法院在2024年案件中,发现抵押人与承租人存在亲属关系且租金明显低于市场价,但未直接认定合同无效,而是以妨碍执行为由解除占有,允许承租人另案主张违约责任。这种审慎态度既维护了执行效率,又保留了承租人的救济渠道。
对于租赁真实性的审查,司法机关已形成标准化操作流程。包括核查租赁合同备案登记、租金支付凭证、物业费缴纳记录等书证,辅以现场勘查、证人询问等调查手段。在浙江某案件中,承租人虽主张租赁合同签订于五年前,但物业记录显示其实际入住时间晚于抵押登记,法院据此否定其对抗效力。这种穿透式审查有效遏制了“阴阳合同”“虚假租赁”等规避执行行为。
四、权利冲突中的利益平衡
抵押权人与承租人的利益协调需遵循比例原则。对于剩余租期较短、租金水平合理的租赁,实践中存在“带租拍卖”的折中方案。北京某商业地产拍卖中,法院在评估报告确认三年租约仅影响5%估值后,采取保留租赁关系的拍卖方式,最终成交价与涤除租赁后的预期值基本持平。这种处理既保障了抵押权实现,又减少了承租人因提前解约产生的损失。
值得注意的是,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不因租赁关系涤除而消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23)渝执复15号案例,即便法院裁定除去租赁权,承租人仍可在拍卖程序中主张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这种制度设计实现了《民法典》第726条与担保制度的衔接,在抵押权人实现债权的为承租人保留了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
上一篇:抵押房产拍卖后所得款项如何分配 下一篇:抽奖翡翠维修服务是否收取额外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