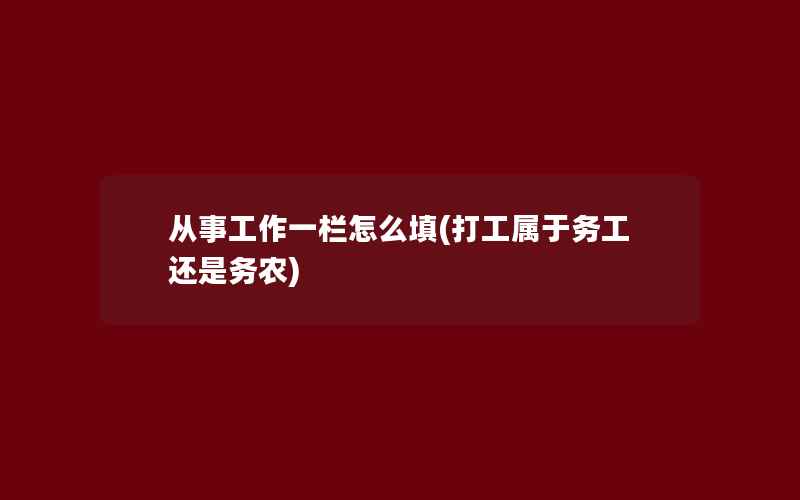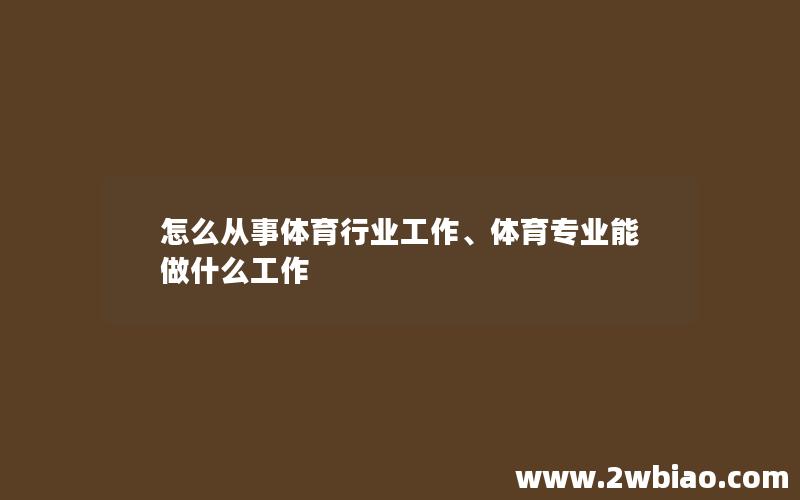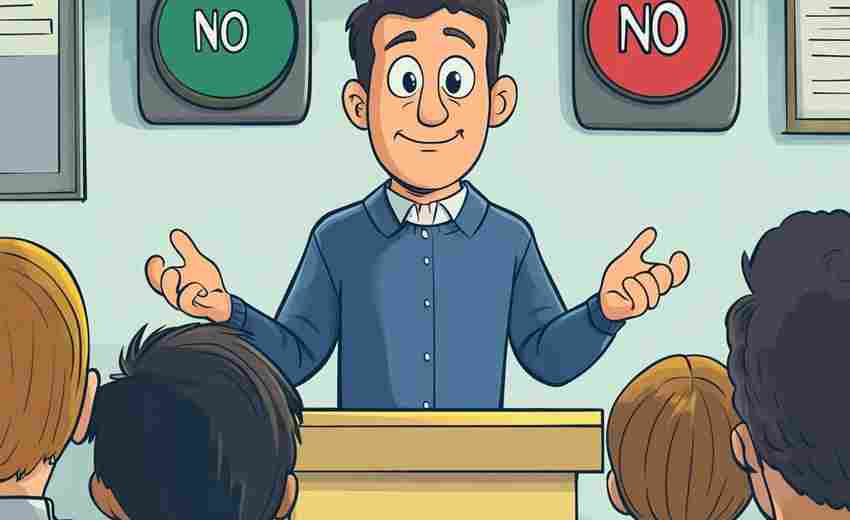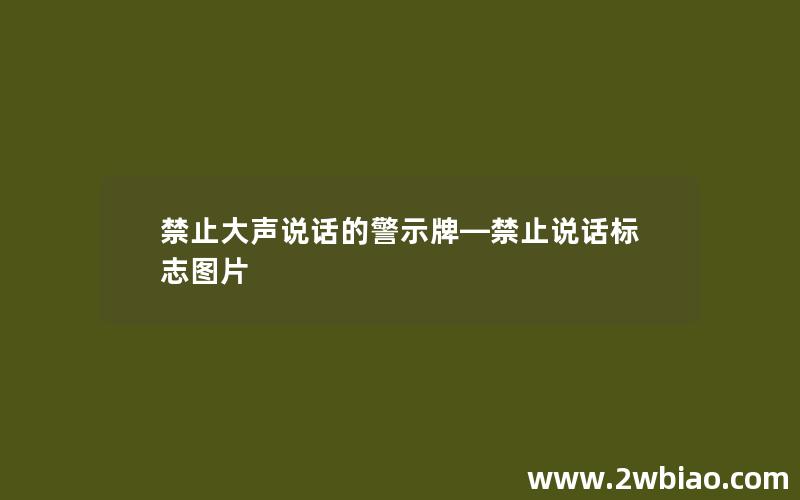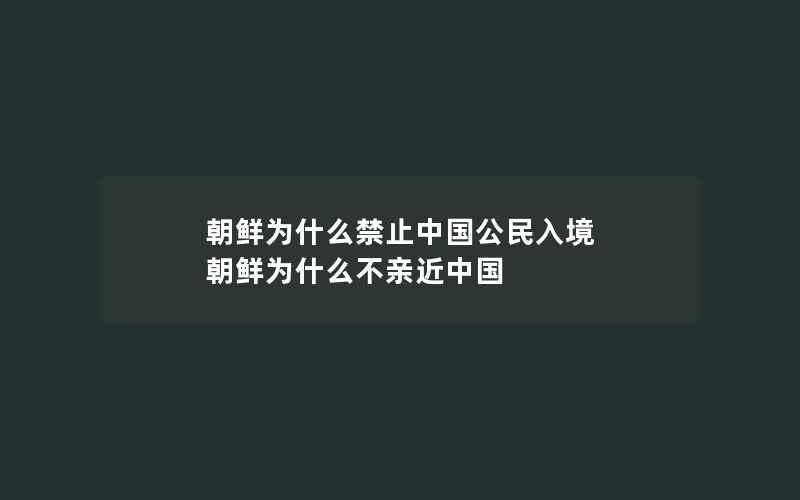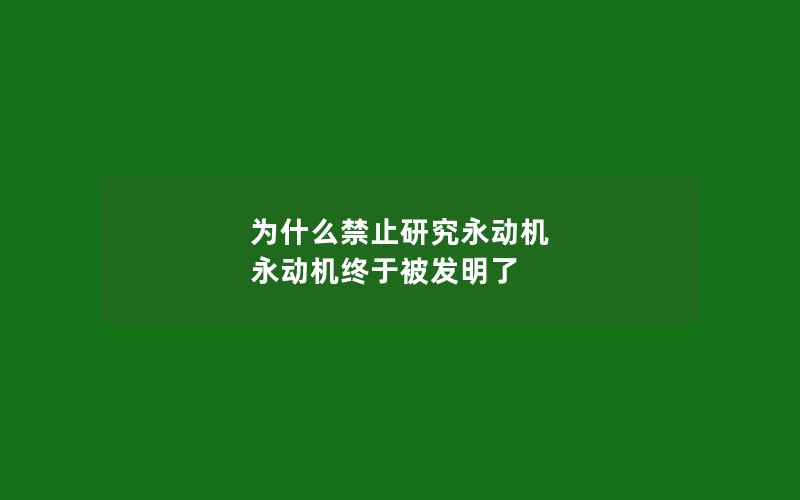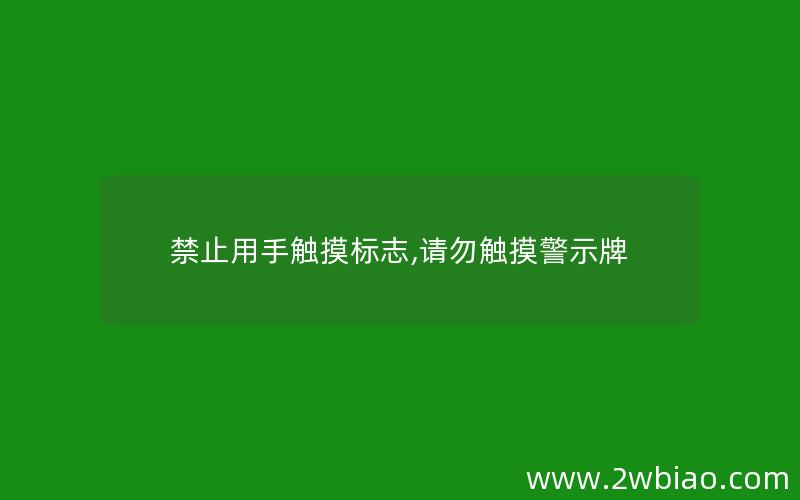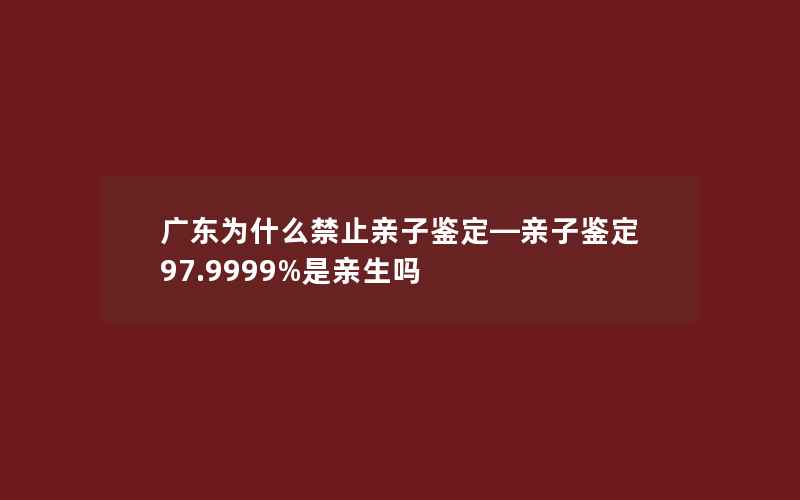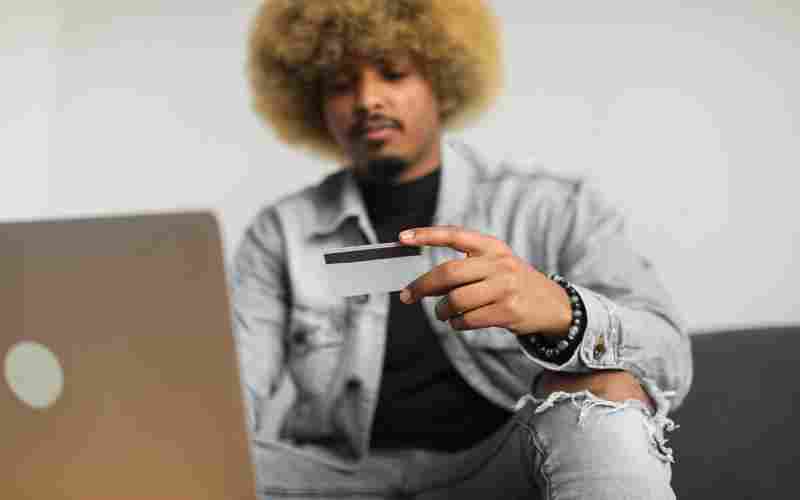未成年工禁止从事哪些类型的工作
在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的现代社会,未成年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始终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全球约有1.6亿未成年人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其中超过半数从事着与其身心发展不相适应的工作。我国作为《儿童权利公约》缔约国,通过《劳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体系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保护机制,明确划定了未成年工禁止从事的劳动范畴。
法律框架的强制性约束
现行法律体系对未成年工劳动保护形成立体化规制。《劳动法》第64条明确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对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工实行特殊保护。这种分层管理模式既尊重了未成年人参与社会实践的权利,又避免了过度劳动对其身心发展的损害。
最高人民法院2021年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某制造企业安排未成年工连续三个月从事高强度金属锻造作业,最终因违反《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被处以双倍赔偿。这种司法实践印证了法律条款的实际效力,也警示用人单位必须严格遵循劳动时间、工作环境等方面的特殊规定。
高危行业的明确禁区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划定的《未成年工禁止从事劳动范围》明确列出矿山井下、有毒有害、高温高压等九大类工作禁区。以化工行业为例,未成年工接触苯系物等化学物质会显著增加白血病发病风险,这类岗位即便配备防护设备仍被严格禁止。
2023年广东某电子厂违规使用未成年工进行电路板酸洗作业的案例引发社会关注。涉事企业虽提供防护服,但医学检测显示涉事未成年人尿液中重金属含量超标3倍。这种案例揭示机械执行防护标准不足以消除职业危害,必须从源头上杜绝未成年人接触高危岗位。
心理健康的隐形威胁
除生理损害风险外,某些特定工种对未成年人心理发展构成潜在威胁。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学研究所的追踪研究表明,长期从事客户投诉处理、债务催收等高压岗位的未成年工,焦虑症发病率较同龄人高出47%。这类工作要求的情绪劳动远超未成年人心理承受阈值。
网络直播等新兴业态中出现的未成年人主播群体更值得警惕。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22年调研发现,32%的未成年主播存在昼夜颠倒、社交恐惧等适应障碍。虽然这类工作不涉及体力劳动,但其对生物节律的破坏和心理健康的侵蚀同样属于法律规制的保护范畴。
国际公约的本土化实践
我国在履行国际劳工组织第138号《准予就业最低年龄公约》过程中,创新性建立了职业学校的实习备案制度。这种制度设计既保障了年满16周岁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权利,又通过教育主管部门备案审查机制,有效规避实习内容超出学生承受能力的风险。
对比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我国特别强调实习岗位与所学专业的对口率要求。某职业技术学校2021年因安排汽修专业学生到建筑工地实习被行政处罚的案例,体现了监管部门对实习性质与劳动强度匹配性的严格把控。
监管体系的现实挑战
新型就业形态给传统监管带来考验。外卖平台众包模式下,部分商家通过虚假注册方式使用未成年人配送员。2023年市场监管总局专项整治中,某平台一次性清退冒用他人身份的未成年骑手达1200余人,暴露出零工经济中的身份核验漏洞。
边远地区家庭作坊式用工仍是监管盲区。云南某茶叶加工坊2022年使用童工采茶的案例显示,传统熟人社会网络中的隐蔽用工,需要建立更灵敏的基层举报响应机制。这种现状要求劳动监察部门必须完善网格化管理,将保护网络延伸至社会治理末梢。
上一篇:未成年工参加工伤保险的最低年龄限制是什么 下一篇:未成熟的榴莲发苦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