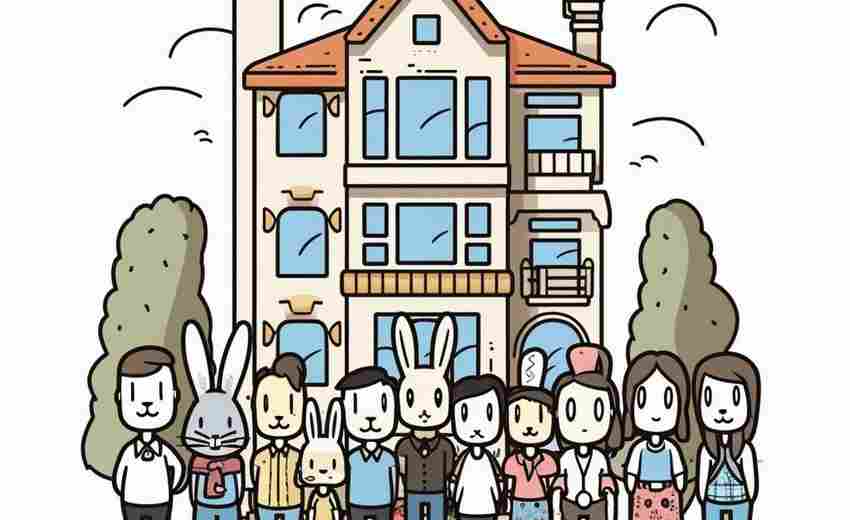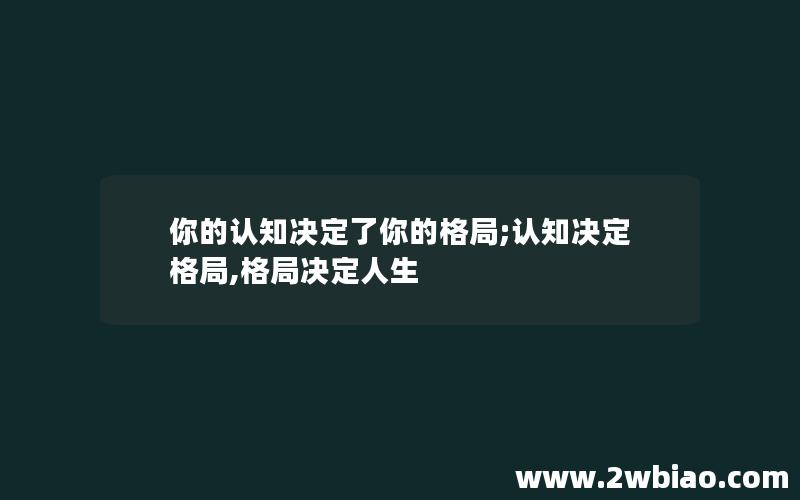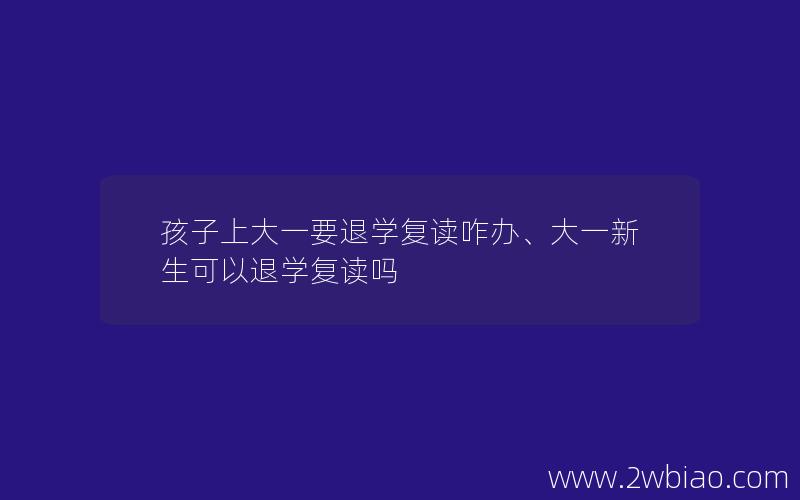退学决定违反教育法规的情形有哪些
教育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不仅关乎学生权益保障,更是依法治校的核心议题。近年来,多起退学纠纷案件反映出部分教育机构在作出退学决定时存在违反教育法规的情形,这些行为往往涉及程序疏漏、依据失当、权利侵害等多重维度,亟需通过司法审查与制度完善实现权力运行的规范化。
程序要件缺失的违法性
程序正义是教育行政行为的生命线。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学校作出退学决定前必须履行告知义务,允许学生进行陈述申辩,并由校长办公会议集体决议。在“谭某诉西南大学退学处理案”中,法院明确指出学校未经校长会议研究且未告知申诉权,构成程序违法。这一裁判观点在“任某不服广东省教育厅取消学籍案”中再次被强调,未经法定程序作出的退学决定必然面临司法否定评价。
程序违法还体现在证据审查环节。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显示,学校在作出退学决定时未实际核查学生后续注册、学习等行为,仅凭单方认定作出处分,导致事实认定与后续管理行为自相矛盾。此类程序瑕疵不仅违反《教育法》第二十九条,更与《行政诉讼法》确立的正当程序原则直接冲突。
处分依据的合法性争议
校规校纪与上位法的冲突是退学纠纷的高发领域。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38号确立的核心原则是:高校制定的校规不得突破法律、法规及规章的授权范围。在“田永案”中,北京科技大学自行增设的退学条件因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二十九条相抵触而被判定无效。类似情形在“小丽诉长沙某职校退学案”中亦有体现,学校以内部招生简章替代法定退学条件,被法院认定缺乏法律依据。
校规解释权的滥用同样构成违法风险。部分学校对“学业成绩未达标”“严重违纪”等概念作扩张性解释,例如西南大学在“谭某案”中将“不合格科目”的计算方式扩大至补考合格科目,这种解释因超出规章授权范围而被否定。司法实践中,法院坚持“最小侵害原则”,要求校方在多种处理方式中选择对学生权益影响最小的方案。
处分必要性与比例失衡
教育惩戒需遵循“罚当其过”的衡平原则。在“大连海事大学张某鹏案”中,法院指出开除学籍作为最严厉处分,应限于考试作弊、学术不端等重大违纪行为,且需考量学生过错程度与悔改表现。而“小丽案”中,未成年学生仅因文身被取消入学资格,法院认为该处理未考虑消除文身的可能性,违背《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十八条的立法精神。
比例原则的适用还体现在替代性教育措施的优先性。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第八条要求学校对不符合招生条件的学生应先采取转学、休学等柔性措施,而非直接注销学籍。在“任某案”中,教育部门未穷尽教育挽救手段即作出退学决定,被认定违反行政管理中的必要性原则。
特殊群体权益保护缺位
未成年学生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受教育权具有特殊保护价值。根据《义务教育法》第五条,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具有不可剥夺性,任何强制退学行为均涉嫌违法。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义务教育阶段的退学决定实行“零容忍”审查标准,如某初中以学生成绩差为由劝退,教育行政部门立即责令纠正并启动问责程序。
残疾学生、患病学生等群体的特殊保护亦不容忽视。《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因病无法学习者应办理休学而非退学,且需经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在“谭某案”中,学校未核查学生长期缺课是否与心理健康问题相关,直接以旷课时数达标为由退学,该做法因忽视特殊群体保护义务被认定违法。
救济机制运行失范
申诉权的实质保障是教育行政救济的核心。《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六十一条至第六十四条构建了“校内申诉—行政申诉—司法救济”三级救济体系,但实践中常出现程序空转。如西南大学在“谭某案”中虽将校规印发学生,却未在退学文书中载明申诉途径与期限,导致救济机制形同虚设。此类程序瑕疵在“中国民航大学李某达案”中同样暴露,学校未依规组建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致使申诉程序无法启动。
司法审查标准的不统一亦加剧救济困境。部分法院对“学术自治”范畴的退学决定采取谦抑立场,但“田永案”确立的审查规则表明,涉及学籍剥夺的行政行为应接受全面司法审查。最新裁判趋势显示,法院开始引入“明显不当”标准,对处分畸轻畸重、违反公序良俗的退学决定予以撤销,如某高校因学生撕毁广告单页索赔万元并退学,被认定构成权力滥用。
上一篇:退出相互宝后原有风险评估结果是否仍然有效 下一篇:退换货流程需要哪些操作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