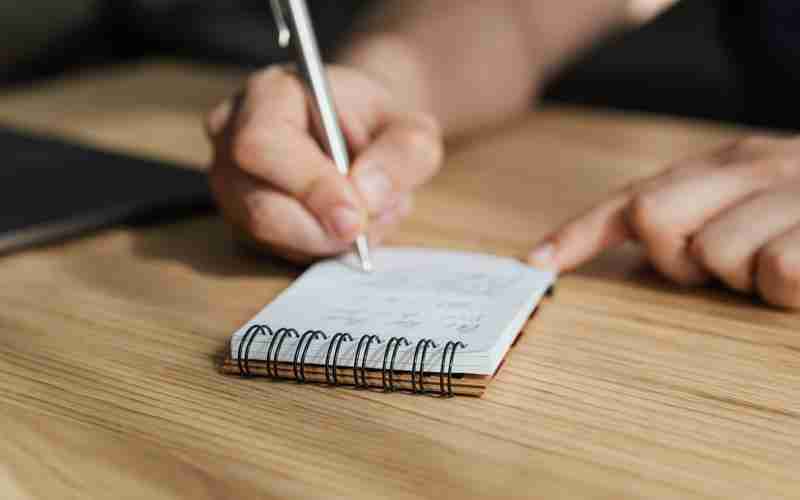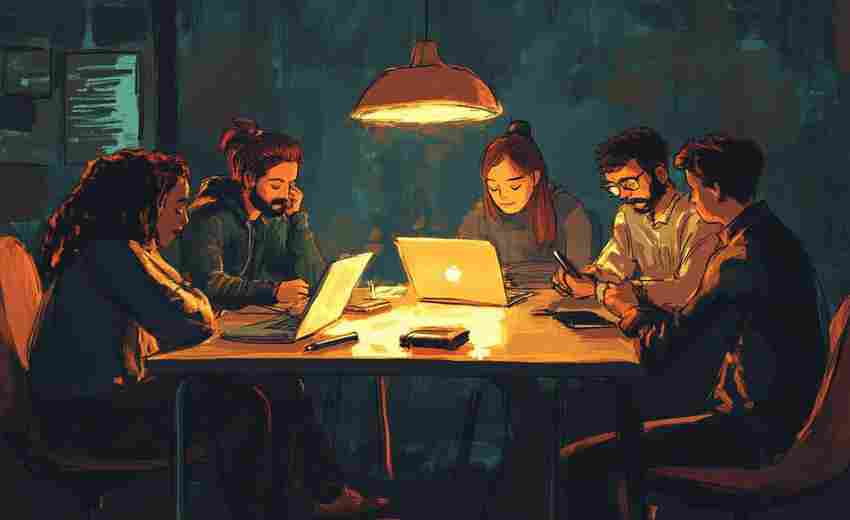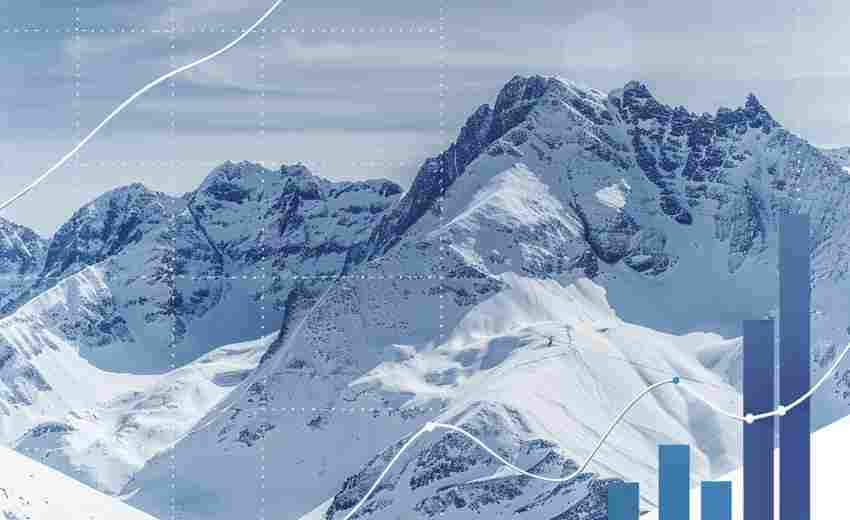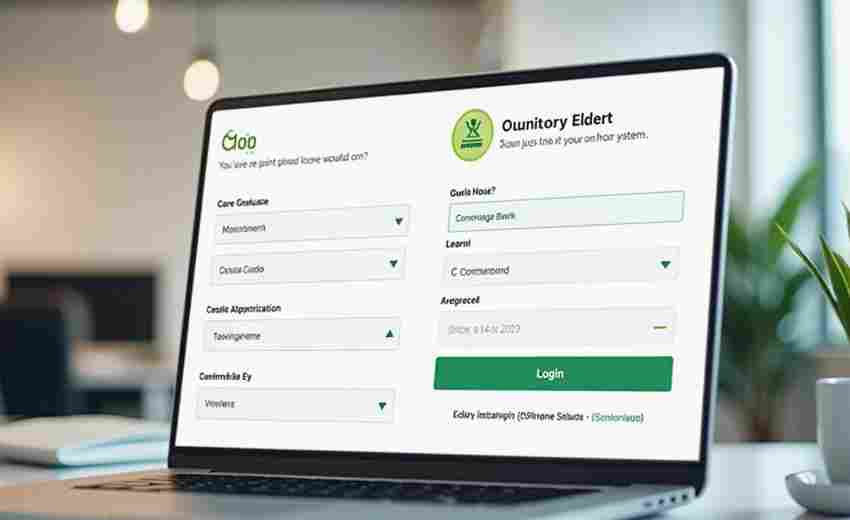中介服务不达标时如何界定其赔偿责任
在房地产交易、商业合作等经济活动中,中介服务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环节。当服务未达约定标准时,如何界定中介机构的赔偿责任,既关乎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也考验着法律对市场秩序的平衡能力。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既要尊重合同自由原则,又要防止中介利用信息优势规避责任。
合同约定与法律依据
中介合同是界定责任的首要依据。《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二条明确,中介人负有如实报告义务,若故意隐瞒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信息,不仅丧失报酬请求权,还需承担赔偿责任。例如,上海某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周某某案中,法院认定买方利用其他中介获取同一房源不构成违约,但利用原中介独家信息则需担责。这种裁判思路体现了对合同条款的严格解释,同时兼顾市场竞争的正当性。
但合同自由并非无边界。若中介合同中存在“对其提供的建议或工作不承担责任”等概括性免责条款,法院会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审查其效力。在山西某公司中介合同纠纷案中,最高法指出此类条款仅能免除中介对交易结果的保证责任,不能豁免其如实报告等核心义务。这种司法态度划清了风险分配与责任逃避的界限。
服务瑕疵的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分配直接影响赔偿主张的成败。根据《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条,中介机构适用过错推定原则,需自证无过错。但委托人仍需证明损害事实与中介行为的因果关系。例如贾某诉上海某商贸公司案中,法院要求居间人证明其服务对合同成立的“决定性作用”,否则可调整报酬。这种举证规则既防止了中介夸大贡献,也避免委托人滥用索赔权。
对于服务瑕疵的具体表现,司法实践形成类型化标准。如上海某房地产经纪公司因未告知税费政策变化导致买方损失,被判按过错比例担责。而深圳某中介机构隐瞒交易对象系内部员工,构成欺诈性隐瞒,需全额返还佣金。这些案例显示,法院对“重大瑕疵”与“轻微过失”采取差异化裁量。
赔偿责任的范围与标准
赔偿范围的界定需综合多重因素。在王某诉北京某房产经纪公司案中,法院将市场份额测算指标限定为实际撮合交易量,否定了以机构规模直接推定市场支配地位的主张。这种计算方式体现了损失填平原则,防止惩罚性赔偿扭曲市场竞争。
具体赔偿金额的判定更具技术性。上海某测量公司案确立汇率损失的计算方法,要求按违约期间央行中间价差额计算。而在房屋租赁纠纷中,中介未核实房屋有毒物质超标,需赔偿租客医疗费、检测费及租金损失。此类裁判通过量化标准增强可操作性,但亦保留法官根据服务费金额、损害持续性等因素调整的自由裁量空间。

特殊情形的责任认定
“跳单”行为的认定存在微妙尺度。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五条虽禁止利用中介服务后绕开交易,但上海二中院在2021年判决中指出,若房源信息属于公共资源,买方有权选择报价更低的中介。这种裁判平衡了契约严守与市场竞争,防止中介通过格式条款垄断公共信息。
房屋质量问题的责任边界更具争议。对于“串串房”甲醛超标,法院通常认定中介未尽空气质量审查义务,但会降低赔偿比例,因租客亦负基本注意义务。而在深圳某案中,中介未审核购房资格导致买方违约,被判承担70%的违约金损失。这类判决警示中介必须提升专业审查能力,否则将面临高额追偿风险。
上一篇:中介不履行合同义务时如何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下一篇:中介服务未达到合同约定标准可否拒付佣金